破译“藏北地书”
——解读青藏高原生物演化的化石密码

“咣咣”,地质锤的一端为柱形,敲来有些沉闷;“叮叮”,另一端呈鸭嘴状,敲来听着清脆。钝的一面震出纹理,尖的一面遇缝劈下,一整块页岩就如同一本被随意翻开的书,两片原本紧密贴合在一起的书页就露了出来。
“今天上午尽瞎忙活了,还没有敲化石呢,手痒痒了。”苏涛下手干脆利落,敲击几下便破开了一块页岩。他指着其中一块上的深褐色小黑点说:“如果在被剖开的岩石上看到这种深褐色的东西,或者有很明显形状的东西,就要仔细留意了,因为那很可能就是一块化石。”古生物学是一门基于材料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就是化石。而要找到化石,却需要一连串的偶然来链接。苏涛说:“一块化石历经千万年的地质变化方能形成,然后再在这辽阔的荒原上被人类发现,这样的几率实在太低了,所以每块被发现的化石都是幸运的,更是我们这些研究者难得的缘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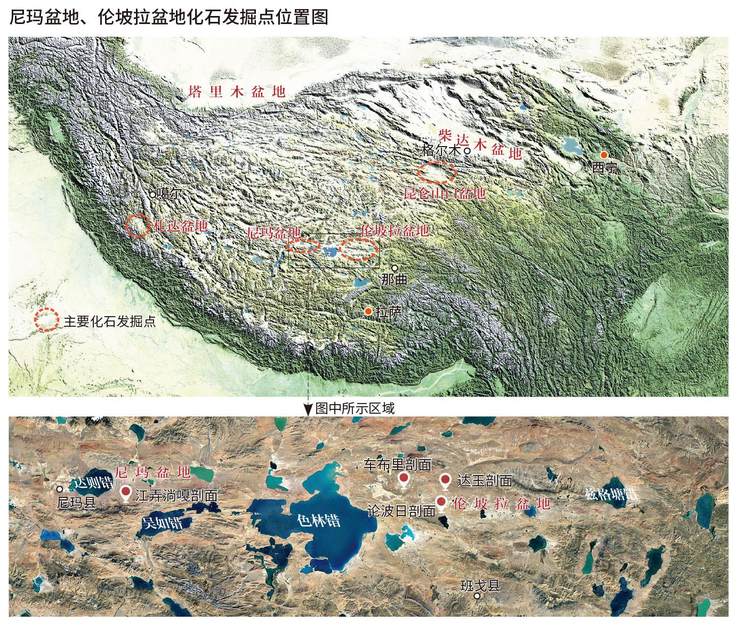


今年30多岁的苏涛来自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古生态研究组,他研究的方向是植物进化、古生态与古环境的重建。2019年6月初在西藏自治区的藏北高原见到他时,他正在执行中国科学院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中古植物科考的部分。今年是他参与此次科学考察的第三年,也是他第16次来到青藏高原。
“V”字地层褶皱:青藏高原沧桑巨变的痕迹
与或沉或轻的敲打声相伴的,是帮工的藏族人欢快的歌声和笑声,以及科考队员们间或交流时的话语声,但所有的声音很快就被呼啸的风声盖住。滑雪镜、户外头巾、口罩、帽子、羽绒服、防风裤,科考队员们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时值6月,虽然沿海地带已经入夏,但在海拔近5000米的藏北高原,气温仅有5—12摄氏度。除了严寒之外,他们在这旷野上工作时最大的“敌人”就是狂风,它携裹着砂石袭来,让科考队员工作时困苦不堪,更可能会让一些质地脆弱的出土化石毁于一旦。
凡中国国家地理网刊登内容,未经授权许可,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它方式使用。
已经本网书面授权的,在使用时必须注明来源。违反上述声明的,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